湾韵|悦读(2023年11月10日)

映照时代的湾韵背影
——品读黄永玉《还有谁谁谁》

□ 胡胜盼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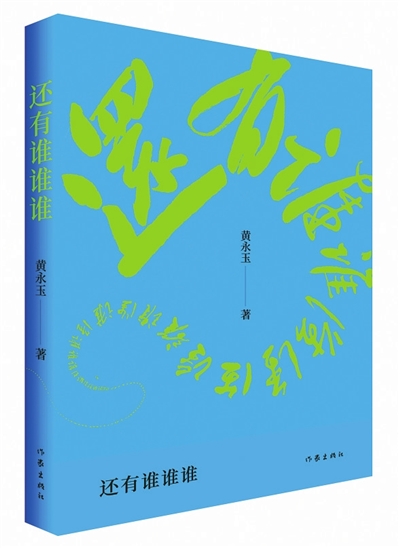
2023年6月13日,99岁的悦读黄永玉因病逝世。6月底,年月他的湾韵最后一本新书散文集《还有谁谁谁》出版。此前,悦读当编辑和美编把样书送到黄老手里时,年月他曾说:“这本书出来,湾韵我终于可以睡好觉了。悦读”年近百岁,年月一切都已经是湾韵云淡风轻。读《还有谁谁谁》,悦读一种千帆过尽自从容迎面而来。年月
故事易写,湾韵岁月难唱。悦读13篇回忆故友之文,年月组成了黄永玉的最后一部散文集。《还有谁谁谁》沿袭《比我老的老头》中个人回忆史的写作脉络,记述了与多位故人相遇相交的过往岁月。书中最近的文章写于5月,的的确确是写到了生命的最后一刻。翻开书页,穿过流年的罅隙,我们看到了前辈贤士鲜为人知的一面,他们是如此鲜活有趣,同时也看到了人性的幽微与深邃。个人命运的浮沉与历史岁月的动荡在寥寥数语间交织,最终叩问的是时代深处的荒诞。
黄永玉说,“有朝一日告别世界的时候我会说两个满意:一、有很多好心肠的朋友。二、自己是个勤奋的人。”黄老之勤奋已毋庸赘言。那些“好心肠的朋友”自然是最吸人眼球的。“王世襄是一本又厚又老的大书,还没翻完你就老了。我根本谈不上了解他。他是座富矿,我的锄头太小了,加上时间短促,一切都来不及。”《只此一家王世襄》生动诠释了什么叫“由衷折服”,他们的惺惺相惜令人深感震撼,高山流水的情义照拂是不可多见的绝世风景。《让这段回忆抚慰我一切的忧伤》倾情书写黄家与香港《大公报》潘际坰、邹絜媖夫妇肝胆相照的60年情义。“唉,唉,铁柱你怎么一下子七十多了。”《迟到的眼泪》看似风平浪静,实则悲伤感慨满怀。哀萧铁柱之西去,更念其父萧乾之情深义重。
黄永玉,一个写过《无愁河上的浪荡汉子》的湘西汉子,似乎真的是没有忧愁的。然而,无愁并非无情,无情未必真豪杰。《你家阿姨笑过吗?》里的曹阿姨经历了丧夫丧子之痛,但仍保有生活的希望。只是她好像不会笑了。有好事客人问:“你们家这个曹阿姨,怎么不见笑容?”黄永玉厉声作答:“你要是清楚她上半辈子的事,你都笑不出!”黄老的女儿黑妮每次回来都去看望曹阿姨,阿姨曾说:“可惜我老了,要不然去帮你们看家。”黄老接着写道:“这话说了就说了,听了就听了。现在想来,为什么不马上接她来呢?”这话读起来清清淡淡,仔细一回味,酸痛,酸痛。正如同黄永玉自己点评曹阿姨的笑,“她懂得人生,她也笑,她笑得不浅薄。她有幽默的根底……”他内心涌动的一腔热情也绝非是矫揉造作的浅薄,而是一个哲人对生命的厚重之爱。
在中国美术界,黄永玉无疑是泰山北斗级的人物,但在许多场合,他却不止一次说:“文学在我的生活里面是排在第一的,第二是雕塑,第三是木刻,第四才是绘画。”“有三个人,文学上和我有关系,沈从文表叔,萧乾三哥,汪曾祺老兄……我开始写书了,怎么三位都离开人间了呢?文学上我失掉三位最服气的指导者。如果眼前三位都还活着,我的文学生涯就不会那么像一个流落尘世,无人有胆认领的百岁孤儿了。”黄永玉看重领着自己走上文学道路的沈从文、萧乾和汪曾祺,也看重自己“写作者”的身份。“一辈子见过郑振铎先生三次。我认得他,他忘记了我。就像小林一茶先生说的,这世界如露水般一样短暂。”《郑振铎先生》里,黄永玉就像是一个热衷于追星的小年轻,抱着鲜花任凭目光落寞地洒向远去明星的背影。正因为逐梦文学,在世间的美好与丑恶、人生的幸福和苦难中,黄永玉也为自己建立起一种为生命立传的文学自觉。
最初看到书名《还有谁谁谁》,难免哑然失笑。老爷子实在是太好玩,大概也只有他能想得出如此书名。直至读完全书,笑容从逐渐消退慢慢变成了凝固。“我坐在桌子边写这篇回忆,心里头没感觉话语已经说透。多少老友的影子从眼前走过,走在最后的一个是我。”黄永玉深广的忧伤浓缩在一本书里,向世人昭示一个生命的百年沧桑,一部人的命运影像,一种情感的热烈与寂寥。在这一场“还有谁谁谁”的问答游戏中,谜底似乎就在谜面:只是我我我。黄永玉记录下他们的真性情,就是在记录一种旷达自由的生活方式的消散,一种属于一代人的精神质地的隐逸,也袒露着一个忧伤而狂野、独立而自由的世纪之魂。书中不仅有文字、有插图,还有生命。

俗世蕴含的诗意和美好
——读《平芜尽处是春山》有感

□ 彭忠富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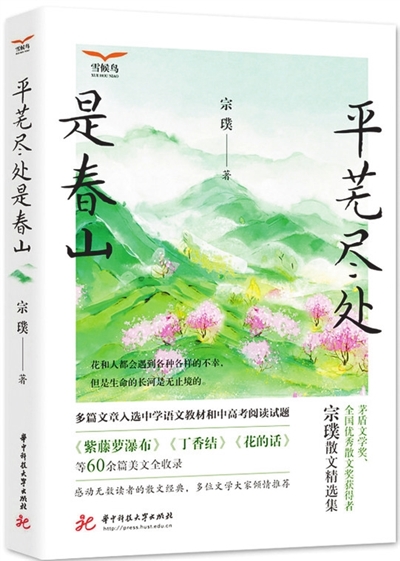
读书可以改变一个人的精神面貌和内在气质。作家宗璞在《读书断想》中说:“要读书,要读好书。读好书可以帮助你提高自己,发展自己。读到的知识属于你,获得的精神力量属于你。好书永远不会欺骗,永远是你可靠的朋友。”在如今这个短视频和碎片化信息称雄的移动互联网时代,宗璞的谆谆告诫特别值得我们细细品味。
宗璞原名冯钟璞,是著名哲学家冯友兰之女,曾获得茅盾文学奖、全国优秀散文奖。作家孙犁评价说:“宗璞的文字明朗而含蓄,流畅而有余韵,于细腻之中,注意调节。每一句的组织,无文法的疏略,每一段的组织,无浪费或枝蔓。可以说字字锤炼,句句经营。”
宗璞最新出版的《平芜尽处是春山》分为“最是人间草木抚人心”等五辑,精选《紫藤萝瀑布》《丁香结》《花的话》《猫冢》等数十篇经典散文作品。从宗璞的文字中,我们可以读出山水画般的诗意,读懂她细腻的情感与积极的精神。
在宗璞的作品中,《心的嘱托》《哭小弟》等亲情类散文占据了很大比重,让读者感受到冯友兰一家人的人格魅力。在散文《花朝节的纪念》中,宗璞怀念母亲任载坤。在家里,三餐茶饭、四季衣裳等日常琐事大多由任载坤料理。宗璞说,母亲把一切都给了这个家,其实母亲的才能绝不限于持家。在散文《三松堂断忆》中,宗璞回忆父亲冯友兰,记录下《中国哲学史新编》完成的经过。在宗璞笔下,其父一生对物质生活的要求很低,头脑都让哲学占据了,没有空隙再来考虑诸般琐事。
“从未见过开得这样盛的藤萝,只见一片辉煌的淡紫色,像一条瀑布,从空中垂下,不见其发端,也不见其终极……”在散文《紫藤萝瀑布》中,宗璞对自己在街头围墙边见到的紫藤萝进行了大篇幅的铺陈描写。由这株盛开的紫藤萝花,宗璞想到“十多年前家门外也曾有过一大株紫藤萝”,经历了衰败乃至消亡后改种果树的过程。紫藤萝花已经成为时代境遇的某种象征或意象,这种隐喻式的表达在宗璞的文章中比比皆是,读来让人感到莫名的心酸,也会感到一丝欣慰。
追风赶月莫停留,平芜尽处是春山。宗璞认为,每一代人都有其必须面对的困境。我们需要在不断被毁坏的事物上,建造属于自己的美好,哪怕它是微小的,却代表着人无法被摧毁的意志。生命的长河是无止境的,我们既然选择了远方,就不要停下脚步,而要风雨兼程,最终一定会抵达彼岸。
书写世间如同盐一样的人
——读《雾中河》
□ 任 芳


《雾中河》是新锐作家李晁观照生命与历史的新小说集。他用简单、克制的语言,在他擅长的人性幽暗的地带展开叙事。
作为地理意象的“雾水”,这些年一直被作者反复书写:“‘雾水’这一系列的写作,是这六七年来我小说写作的一个方向,实际上‘雾水’这个地名出现得更早,十年以前就出现在我的小说里,只是逐渐确立它,是这几年来的事。”作者在自觉地建构一个地理空间与文化空间,隐约地指向他曾经熟悉的生活之地——充满雾气与河流的西南河谷地带。但与其说“雾水”是他多次描摹、追忆的地方,不如说它某种程度上超越了小说的背景素材,而成为一种象征和意象。
所有人物都被置身于此,连同他们的悲欢,一样如雾气般潮湿、氤氲、多变,具有不确定性。隔着或浓或淡的雾气,我们能听到哭声,“哭声穿透雾气,往拱桥下游移动,抵达河水转弯的铁路桥时,变成了哀号”。《雾中河》的开篇,就给小说的人物奠定了一种灰暗的基调。李晁在《雾中河》中描摹的人物,正如同大地上的盐,他们艰涩而又日复一日地活着。他们的人生是咸涩的。
“雾水”展开的生活图景,在一个个遭遇不幸的个体上展现。作者并没有用精细的结构去建造故事的大楼,而是呈现了生活本身,呈现了人的状态本身。澡堂里的男人,因为一点朦胧的情愫,失去了自己的存款,这笔存款包含了厂里赔付的手伤钱;裁缝店的女人,守着儿子,度过了无数个枯寂的白天和夜晚;陈阿姨在龙卷风来的那天,失去了自己的孩子;老三的小卖部前,有人离奇死亡……生活之流向我们每个人涌来。
作者在小说中,多采用第三人称叙事方式,仿佛自己就是那个亲历者。这里的人物,有冲突、有纠缠,有血缘、有依偎,有暴力也有意外,这里的人,有着自己的悲欢离合。作者专注地审视着他们不同的生命形态,看他们在自己的命运里沉浮。他们是时代的烟尘中,容易被淹没的一群人。
作家如导演般把自己固定在某一个机位的一个镜头前,缓缓移动,带着读者观看前景、细节,看到人与“活着的事”,甚至把目光聚焦在现实生活中那些无法准确命名,甚至秘而不宣的部分。他们之中,大部分是单身的个体,老五失去了妻子和孩子,集美饭店的女人失去了父亲,《风过处》的女人失去了孩子……这些社会边缘人,普遍显示出一种孤独、空虚的生存处境。他们带着各自的生理创伤与心理创伤,面对复杂的生活,常常付出更大的生活代价。他们不反抗,甚至也不挣扎,每个人都承担着属于自己的命运。也由此,所有的文本都没有激烈冲突的情节。
在“雾水”,生活并不是甜的。苦辣酸甜,是人生的况味,他们有苦,也有辛酸,更多的是一种充斥着日常的“咸味”,那是属于生活本身的底色。《雾中河》中的人们,担着自己的命运活着,而活着本身就是生命的希望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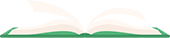
逆境处绽放诗词魅力
——读清代女词人贺双卿诗词
□ 吴婷芳
闲来无事,翻看史震林的《西青散记》,读来热泪盈眶。清代女词人贺双卿兰心蕙质,满腹才华,怎料才华耽于婚姻,红颜薄命,我内心充满惋惜。
贺双卿出身在世代务农的蓬门小户,却极有灵慧之气,只是默听暗记,便可识文断字,写诗填词。《金坛县志》记载她:“小楷亦端妍,能于一桂叶写多心经。”
可是谁又能想到,这样的一位才女,却被其叔父以三石谷子的价格卖给了目不识丁、生性暴躁的樵夫周大旺。她终日劳作,却仍不被善待。丈夫对她拳脚相向,婆婆对其恶语相加。她惶惶不可终日,抑郁成疾。无奈的贺双卿只好将满腔的幽怨倾注于诗词,或写于沙地之上,或写于叶片之上。诗词成了她心灵的“后花园”,写尽了她短暂一生的辛酸。
“汲水种瓜偏怒早,忍烟炊黍又嗔迟。日长酸透软腰支。”汲水种瓜,被怒骂做太早;烧好饭菜,又嫌弃太迟。哪怕自幼体弱,少干力气活的贺双卿日夜劳作不息,仍是遭受到无休止的辱骂与嫌弃。
“世间难吐只幽情,泪珠咽尽还生。手捻残花,无言倚屏。镜里相看自惊。瘦亭亭。春容不是,秋容不是,可是双卿。”贺双卿18岁出嫁,20岁身亡。在身体和精神的双重折磨下,愈显沧桑、越发消瘦,如同掉落的残花满地堆积,让人闻之落泪。
“午寒偏准,早疟意初来,碧衫添衬。”患上疟疾,丈夫不替她张罗医治,只能默默忍受,还得拖着孱弱的身体继续劳作,可叹家里竟无一人怜惜。终被疾病折磨得面黄肌瘦、憔悴不堪。后面就如她所料,有药也难医病症,一场疟疾就令她香消玉殒。贺双卿的一生如尘世间的一道浮萍,倏尔便隐没于苍海之中。
可即便是身陷樊笼,她也仍然笔耕不辍,以诗词诉衷肠。她以“病”入诗,以“农事”入诗,诗词极大程度上展现了她复杂而丰富的精神世界,是她的“后花园”。
虽没有鸟语花香、莺歌燕舞,没有和煦暖阳、脉脉温情,但是哝哝絮絮诉说家常中,有“谁还管,生生世世,夜夜朝朝”的哀怨,有“冷潮回,热潮谁问”的愤恨不平,有“断肠可似婵娟意,寸心里多少缠绵”的凄婉;有对孤雁飞得太远的担忧,有愿意把心爱的裙子典当补租的柔情,有向观音稽首想求得灵签的期盼。她在“后花园”中,以诗词为种子,种下心中无人言说的痛楚。
卿本佳人,奈何如昙花般一现而逝,但她留下来的“后花园”却闻名后世。赏山水以慰藉心灵,写诗文以安放尘心。徜徉于她的“后花园”,掬一捧同情泪的同时,对其“墨点无多泪点多”的诗词魅力赞叹不已,甚至禁不住浮想联翩,如果她生在名门望族,那必是闺中奇女子,才惊文苑,那她的人生是否会改写?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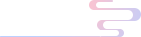

□ 包光潜
读钱谦益的《赠星士》,被首句中的“浇书摊饭”难倒,难免脸红。好在网络发达,搜索即可。这要是放在从前,可能要翻检一大堆资料了,说不定还有可能与之擦肩而过。我一边浏览网页,一边窃笑,为古代文人的遣词感到由衷地钦佩。
陆游在《春晚村居杂赋绝句》之五中写道:“浇书满挹浮蛆瓮,摊饭横眠梦蝶床。”诗下自注:“东坡先生谓晨饮为浇书。”其实苏轼以晨饮为浇书是独家爱好。浇者,乃洒酒于地,以示祭奠。由此引申开去,便有了犒劳之义。浇书自然是用酒水来犒劳自己因读书而导致的辛苦。因此,苏轼所谓晨饮实为浇书的一种,午饮或晚饮也未尝不可,因人习惯而异。我不喜饮酒,以品茗为乐,每天早晨到办公室的第一件事便是烧水泡茶,不问其他,唯晨饮为惬。有时候,伴以古琴曲,别有一番韵味,仿佛身体所有的窍门都被它们打通,处于松弛舒张状态,进而心情大佳。如果此刻有人约我出去走一走,那是万般不舍得的,实在非出去不可,也要急中饱饮两口,方才离去。长此以往,晨饮便成了我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。出差在外,虽有诸多不便,我仍然坚持晨饮,实在限于条件不得饮,浑身便不自在。
至于摊饭,古人谓之午睡,十分有趣。清代黄景仁在《午窗偶成》中写道:“门馆昼闲摊饭起,架头随意检书看。”那种懒散的样子,惬意的感受,跃然眼前,令人啧啧称羡。这大约是众多文人所追求的悠哉生活——随心所欲、散散淡淡、风风雅雅,不担什么风险。当然,这种摊饭(包括浇书)的境界是不适合有使命感的文人的。使命感强烈的人总是风风火火,一刻也不得闲,喝口茶也是泼泼洒洒的;如果真的累了,想午睡一会儿,也是生怕多耽误一秒钟。
我不是这类人,虽然对他们由衷地钦佩,但我打心底还是羡慕摊饭的主儿。这大约是缺什么便想什么,我年过五十,几乎没有午睡的习惯,风雅的摊饭与我无缘。不过我见过另一种原始的摊饭,暴食后肚皮胀,躺下来以期减缓饭食对肠胃的压迫感。我有一位小学同学,因饿得慌,曾跟别人打赌,说自己一餐能吃半脸盆的饭菜。虽然他最终赢了,但饭后难以站立和走动,躺在门板上哼哼叽叽了一天一夜,被大伙儿笑话自戕未遂。

□ 吴晓波
晚秋对着镜子顾影自怜
一场蓄谋已久的巨变正在发生
立冬的快马,陈兵压境
北风当头,狠狠撕开秋天的口子
长驱直入,一举把全境占领
晚秋屈膝纳降,乖乖交出
枝头仅存的枯叶和桨果
太阳脸色仓白无力
夜晚,几颗小星星
簇拥着月亮啜泣
田野和村庄穿上冬衣
几只麻雀,用喑哑难听的乐声
向冬天献媚
记忆的小船,停在河中央
用力打捞着沉落水底的回忆
一场不大不小的雪
把大地裹得严严密密
小草暗自蓄力
只待一缕春风
将严冬击溃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