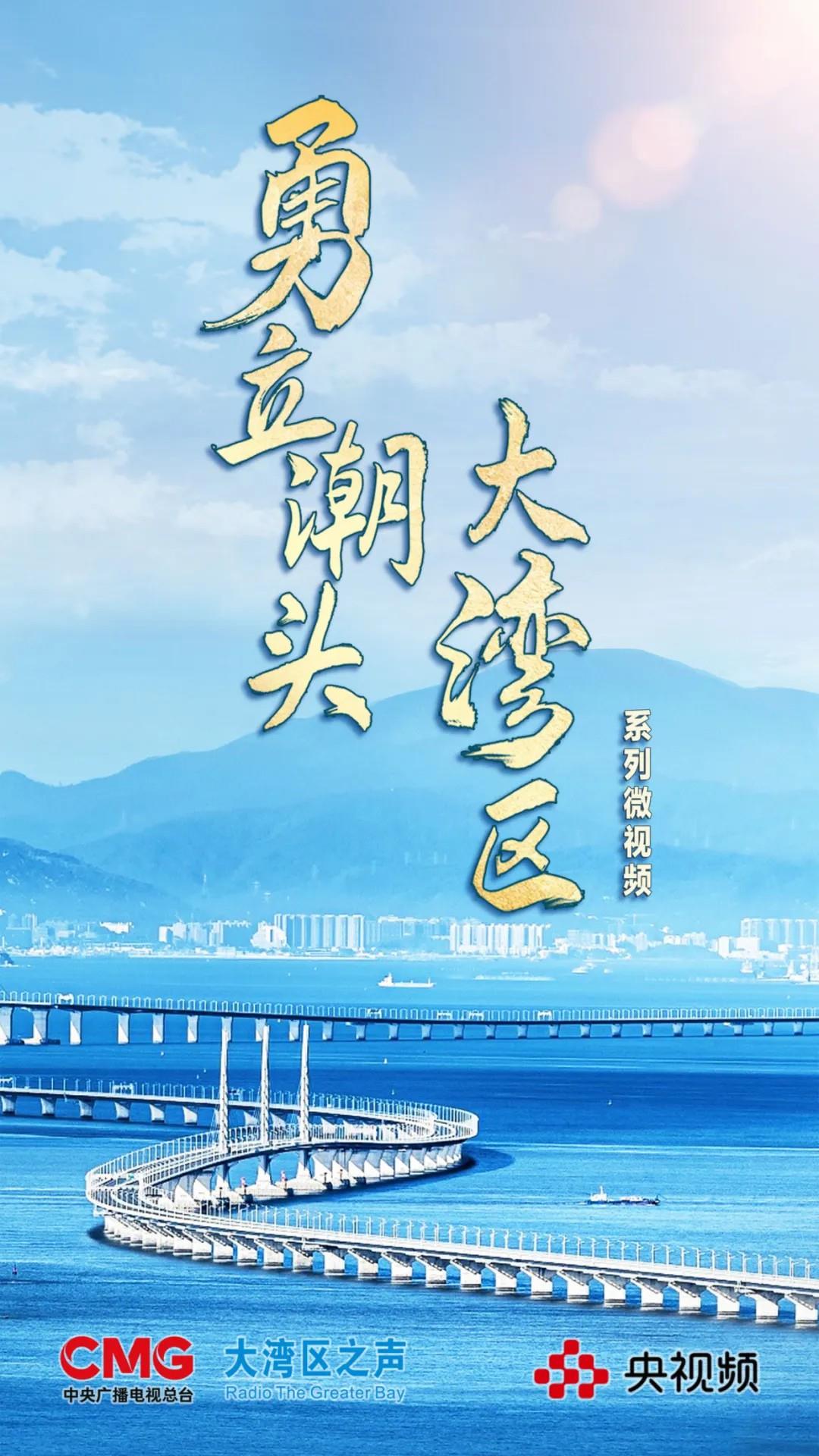勇立潮头大湾区丨低空经济万亿级风口,大湾区乘势高飞!
休闲
2024-06-27 00:23:59
0
沙特阿拉伯近日公布
将启用无人驾驶“空中出租车”计划
采用的勇立正是“湾区制造”
这批由广州亿航智能提供的
无人驾驶电动垂直起降航空器(eVTOL)
在低空环境中沿直线飞行至少30公里
最高时速可达130公里
为人们的出行带来更多便利和舒适
今年4月
广州亿航智能“EH216-Se”eVTOL
成为全球首个三证齐全
无人驾驶载人飞行器
标志着“空中汽车”已具备量产资质
打“飞的”上班或成现实
空中交通新图景更令人期待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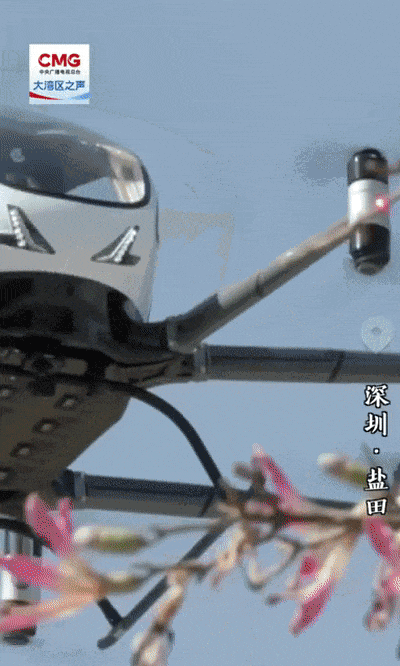
今年以来
广州、深圳等多个湾区城市
竞相打造“天空之城”
低空通勤等无人机载人场景
频频上演
2月,潮头乘势大湾区“空中的大湾低空士”
跨城跨海全球首飞
“盛世龙”eVTOL
搭载5位模拟人
从深圳飞往50公里外的珠海
将单程2.5至3小时的地面车程
缩短至20分钟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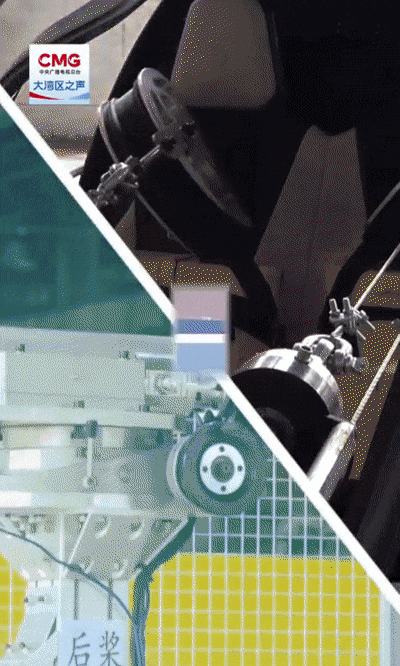
5月,深圳“湾区之翼”起降场建成
未来满负荷运营时
每天可起降
40到50架次无人驾驶飞行器
满足乘客80到100人次
在万米高空和广袤地面之间
大湾区创新城市空运系统
以数智化技术为依托
低空经济乘势起飞
大湾区多个城市
瞄准低空经济
打造“空中的区丨大湾区”
珠海“双航展”龙头带动
多地试点无人机低空领域开放
广州开发区发布“低空10条”
布局千亿级低空经济产业集群
深圳出台全国首部
低空经济地方法规
支持社会资本参与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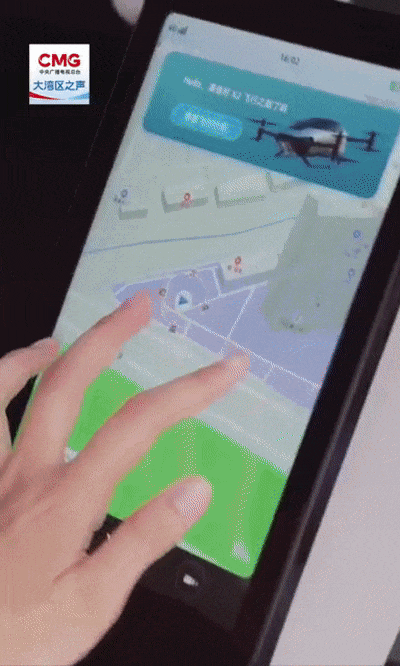
2023年中国低空经济规模
超5000亿元
增速达33.8%
2030年有望达到2万亿元
低空经济
作为新质生产力的代表
在敢为人先的大湾区
正迎“风”而上
展翅高飞